
本版导读
致文学青春的足迹
文章字数:1,571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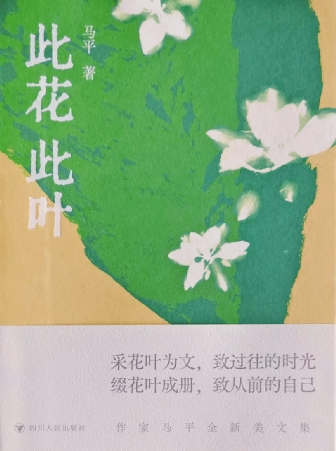
奉友湘(四川)
马平的新作《此花此叶》,腰封上有两句话:“采花叶为文,致过往的时光;缀花叶成册,致从前的自己。”我相信,这是马平的心声。我可以理解为“致文学青春的足迹”。
青春的足迹,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成长史。我一直很惊奇,马平如何从一个乡村教师,成长为一个著名的专业作家。《此花此叶》便为我提供了寻觅答案的无数线索。一个个片段,一个个画面,也就是一朵朵花,一片片叶,一枝枝杈,共同构建了这棵繁茂根深的文学大树。
马平这部新作从写父亲的《朗声》开始。兄弟姊妹五人从小都怕父亲的大嗓门。这嗓门显示了他严肃而爽朗的个性,连清嗓子都具有特点:第一声高亢,第二声低回,第三声响亮。他的大嗓门是他职业的得意武器,据说站在山顶,都可以听到他在山腰教室里讲课的声音。而他的学生们,则在他的大嗓门中日复一日汲取着知识的营养。家里的几个孩子也在父亲“不准这样、不准那样”的大嗓门中体会到严父仁心的爱意。马平本人,也在父亲朗声而讲的故事中,得到了文学的启蒙,在父亲晚年要写小说的激励中获得创作的动力。他由衷地写道:“近年来,我的创作有了一点爆发,好像就有父亲的力量加入进来。事实也正是那样,我不想写或者写不下去的时候,好像总能听到他的喊声。”
父亲的“朗声”让马平的文学之树生根、抽条,节节成长;而母亲的“和声”则为其浇水、施肥、守护,让其健康繁荣。
高堂的健康让马平十分欣慰。母亲83岁,说话既清晰又流利,“脆亮的声音,从没有一点苍老的迹象”。她从嘉陵江河西嫁到河东,首先从口音的改变显示她对婆家的认同,但坚定地守住了她那特有的脆亮。她用生动的乡土语言滋润着马平的文学之树:“日子还长得牵藤”“变了泥鳅哪还怕泥巴糊眼睛”“麻线总是从细处断”等等。她还用做鞋底抽麻线时的“丝丝”声,喂蚕吃桑叶时的“沙沙”声,打连枷时的“啪啪”声,串起马平的文学镜头。正是在母亲的身教下,他一天天懂事,知道在母亲下工时帮助扛锄头,陪伴母亲回家。他深情地写道:“我那一点懂事,或者说,我那一点思考,都由母亲一点一点调教出来。”母亲的声音对自己影响之巨,马平在文中承认:“我知道,我写下的句子哪些出自母亲之口。她当年扎鞋底时对待每一针的那个态度,正是我写作时对待每个字的态度。这些年来,我在写作上一直学着母亲咬针的那个狠劲,却一直学不到家,我署名的那些林林总总的作品,并不能保证针针线线都经得起检验。”我知道,这是他的自谦,也是他的追求。
一棵文学参天大树,除了枝干、树杈,还得有繁花点缀。于是,马平在“雪梨花”盛开的时节,领会到文学启蒙的艰辛。“冬天快来的时候,雪梨花突然在都市里照亮了我,让我感受到了寒意,也让我感受到了芳香”。
除了雪梨花,还有“铁花”“灯花”“窗花”“稻花”。在《稻花》里,我读到了马平从的蜕变。对文学的追求,让他胸中已开始有了锦绣的文字。稻田里成群结队的红蜻蜓,成了一种绝妙的成功象征:“那一团一团的红蜻蜓,起起落落,懒懒散散,兀自让稻田升起了暖色的轻烟。我看出来了,它们不是来标注季节的,而是来扮演花期的。它们要以爱情或是别的什么名义,完成一场别开生面的开花。它们降在了哪一片稻穗上,那一片金黄,就会绽放出鲜红的花朵。”
马平认为,“一部文学作品里,光点不是可有可无的,只不过几个字就够了”。他向读者传递着文学的意义:“我是想说,我们需要文学,有时就是需要它的一个亮点,以及一丝抚慰一丝体贴。我们有时并不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宏大,反而需要它给我们带来细弱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文学小不过一个光点,大不过一团光晕。文学的光亮,似乎就是这样不经意间从细微之处发散出来,然后星星点点凝聚起来,辉映我们缺少光泽的生活。”
这是马平对文学多么深切的感悟!他以自己几十年的文学创作功力,凝聚成字字千金的秘诀。我们通过他这棵文学大树上的一枝一杈,一花一叶,可以欣赏到他文学之路上成功的成团的红蜻蜓。
发布日期:2025-04-23



